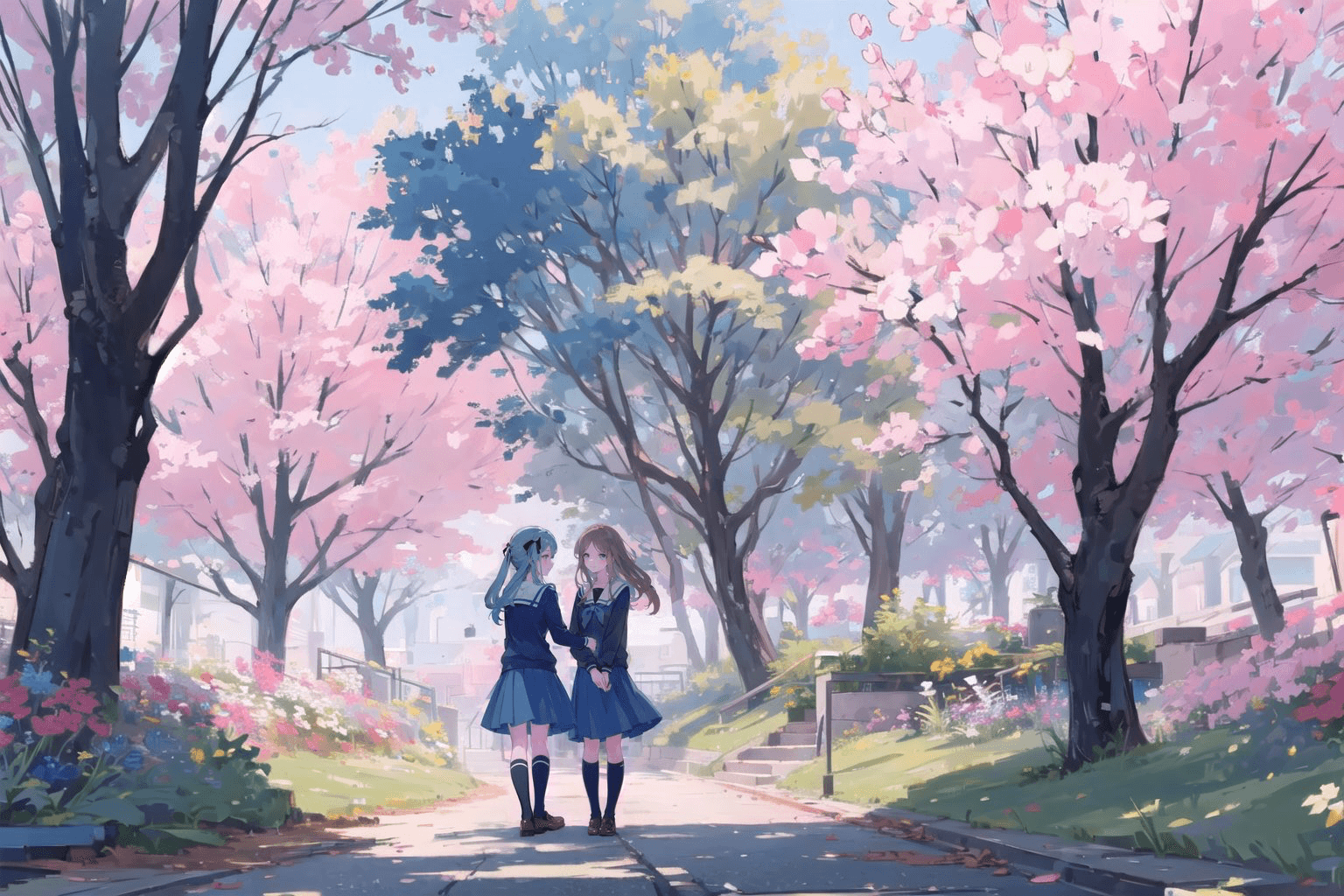东雪莲第一次听《风雨无阻》,是在他的自行车后座。
那时夏末的风卷着梧桐叶,他单手环着车把,另一只手拎着给她买的热奶茶,耳机线从校服口袋里拖出来,一半塞在她耳朵里。李宗盛的嗓音混着车轮碾过落叶的沙沙声,「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,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」,她偷偷数着他T恤后颈被汗浸湿的纹路,觉得这辈子的安稳大概都在这了。
他们说好要考去同一个城市的大学。他成绩不好,却总在晚自习后蹲在她教室窗外,等她出来时晃着手里的错题本,说「这道物理题我琢磨透了,你看」。她知道他是为了能和她多待一会儿,就像她总在他练球的篮球场边放一瓶冰镇可乐,标签上写着「加油」,字迹被水汽晕开也没关系。
变故是在填志愿那天。他的父母突然要带他去南方做生意,他红着眼眶在她家楼下站了整夜,手里攥着两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,一张是她心仪的本地大学,一张是南方的专科。「雪莲,等我回来,」他声音发哑,「最多三年,我一定风风光光地回来娶你。」
她没哭,只是把那副他送的耳机塞回他手里。「你听《风雨无阻》里那句,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,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』。」
后来的日子像被按了快进键。她在北方的秋天里收到他寄来的明信片,背面是南方的椰树,字迹潦草得像他打球时的身影。他说「这边雨多,总想起你怕打雷时往我身后躲的样子」;她说「学校的梧桐又黄了,你教我修的自行车链条还没坏」。
直到有一天,明信片上的地址变成了陌生的城市,邮戳盖着她不认识的邮局。他说「家里生意出了点事,可能要再待几年」,语气里的疲惫像隔着信纸都能渗出来。她回信问「那我们说好的呢」,却迟迟没等来答复。
再听到《风雨无阻》,是在毕业聚会上。KTV的屏幕里闪过歌词:「拥有够不够多,梦的够不够好,可以追求,不认输。」她端着酒杯走到窗边,手机里弹出一条消息,是他发来的婚纱照,新娘笑靥如花,背景是南方那片她只在明信片上见过的海。
他没说对不起,只发了一句「这首歌,我一直存着」。
东雪莲删掉那条消息时,窗外正下着雨,像极了他离开那天的天气。她想起多年前的自行车后座,他问「你说我们以后会不会分开」,她当时靠着他的背,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洗衣粉味,说「才不会」。
原来有些风雨,不是两个人手牵手就能挡住的。就像歌词里唱的,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,剩下的风雨,得自己扛着走下去。她慢慢喝干杯里的酒,酒液有点苦。像那年分享却又害羞没喝完的可乐。
(文章转载自评论区)